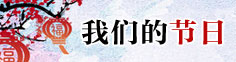文明创建
碧嶂连云峻,丹梯傍涧弯

善坑村楼氏宗祠的古戏台

山脚的古岭淹没于善溪水库中

荒草丛生的善溪亭
如今,我们出行时,可以选择乡间小路、城市道路、省道或国道,出行路径很多元。但如果穿越回古代,脚下的路又该叫什么呢?从“道”到“径”,从“衢”到“阡陌”,古人用不同词汇精准定位。其中,驿道就是由官方修建的陆地交通主通道,主要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官员巡视,兼具军事防御、人员往来等功能。
驿道在古代被视为“大道”,也就是当时主要的官方道路,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古代对驿道的建设也有着统一标准:宽约一丈,可供双马并行。据《义乌市交通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境内即辟有驿道。”乌伤县(今义乌)北接诸暨、南邻大末(今龙游),“婺凡八邑,建自秦汉者,必首乌伤”,因地处越中,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枢纽地位凸显。自古以来,驿道便为交通往来提供了诸多便利,在国家治理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根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从诸暨宣何街(今宣何村)进入义乌境内,沿途经善坑、楂林、苏溪、县城、义亭等,随后进入金华。该段驿道在义乌被称为“杭金古道”,全程为人行道。其中,处于义乌与诸暨交界处的“善坑”,在当时驿道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
据《万历义乌县志》记载:“善坑,去县北五十里,坑深五里,北入诸暨界。”另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善坑岭,县北五十里。由邑达诸暨孔道(指驿路、交通要道),其地为一县之要害,旧建岭头铺(原称善坑铺)于其上。”又见《民国义乌县志稿》记载:“善坑岭,岭高一百十四丈五尺。自楂林市(指集市)北少东、行折而北少西,至此十二里五分,与诸暨县分界。”
可见,善坑岭当是连接义乌与诸暨的分水岭,因其独特的地势成为“会稽险塞”。这里林木葱郁,溪流清澈,奇石嶙峋,险隘藏秀。在其岭顶,更是险峻奇绝,因取其“扼守要冲”之义,故被称为“善关”。这是往来众生必须逾越的天堑咽喉,旅人登临岭顶,顿如窄径悬空,峻极生韵。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途经此关隘时,有感而生,遂作《善关》诗一首。其诗云:“碧嶂连云峻,丹梯傍涧弯。鸡鸣春屐过,静气满深山。”
熊人霖,江西进贤人,明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崇祯十一年(1638年)任义乌知县。此诗描绘了“善关”的独特景色,熔铸了诗人的丰富意象,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你看,这翠峰高耸入云,陡峭的石阶宛若丹梯,依附着古老山岭蜿蜒而上。一旁的山涧潺潺流淌,仿佛也一路伸向了云海深处。春晨鸡鸣声中,旅人脚踏木屐,步过露湿的石阶,踏散缭绕的山岚。随着屐声渐行渐远,身后只留下一片静寂,整座深山愈发显得空灵渺远、神韵非常。
在此诗中,熊人霖还对“善关”作了注释:“善关,义乌北六十里。”从诗题的字面理解,似乎还含有更深层的意蕴:善关之“善”,非指地形之便,而是人与自然达成的高度默契。面对此情此景,诗人以“碧嶂连云”写其高远,以“丹梯傍涧”绘其奇崛,更以“鸡鸣屐响”点破空山之寂。屐痕与苔色相映,人语与山气交融,于有声处闻大寂,在险绝中见从容。人行关隘,松风满怀,非是山峦低首,实乃行客心已越千峰。
险岭穿霄贯南北
善坑是义乌通往诸暨、杭州的咽喉和门户。在《崇祯义乌县志》之“疆域”中这样写道:“东北到诸暨县界五十里。地名善坑,自界至诸暨县治六十里。善坑系官路,铺递连络,行旅肩摩,通东越咽喉,开上江门户,此疆域之巨防也。”熊人霖在他的另一作品《卿云门》中解释道:“通绍兴、宁波诸郡,出于其途,有梁曰酥溪,有山曰善坑,盘互险峻,屹若重关。颜曰‘绾枢吴越’。”
一道山岭,气象万千,险奇并生,令人顿生敬畏,亦引人骋怀遐想。据善坑岭附近的村民介绍,早在数十年前,善坑岭还完好无损。岭上许多路段都是就地取材,将天然的山体凿成石阶。在地势稍平处,则有青灰色的条石铺于岭中,两侧嵌有鹅卵石。其中,岭顶大致就处于今燕窝村(古时又称“燕窠”),岭脚则一直延伸至诸暨的宣何街,岭长约有5里,这也就是古县志中所写的“坑深五里”。处于宣何街的一侧,沿险峻的山崖凿有一百余级石阶,仿佛是靠在峭壁上的长梯,下临深涧。这就是当地人所称的“百步升”。
即便如此险峻,善坑岭一带的西坞、善坑、芦柴等地村民,也能拉上手推车过岭,前往宣何街赶集。古时的宣何村是一个热闹的市镇,店铺林立,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过往客商留下来住宿的甚多,故又称为宣何街。
手推车要翻过如此险峻的山岭,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自是掌握了上下岭的门道:必须要有两人携手,前面的人抬一次手推车,车轮才能上一个台阶;下岭则相反,要让车轮下台阶,必须让前面的人顶着,以此循环往复。
善坑岭系金、衢、严(州)、台、温、处(州)与杭、苏等地往来的通道。每年正月至三月间,浙江“上八府”(以钱塘江为界,江南的宁、绍、台、温、处、金、衢、严等八府)的民众前往“下三府”(杭、嘉、湖等三府)工作,至下半年的十一月后返家,都要途经善坑岭。在每年八九月间,每日则有数以百计的香客路过善坑岭,他们从苏、沪、杭、嘉、湖、绍等地前往永康方岩烧香。
由于善坑岭地理位置特殊,它还是各方军事力量争夺的焦点,见证了不知多少烽火狼烟、铁马金戈。地处善坑岭附近的芦柴,古时为戍守处。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芦寨(通‘柴’),在县东北四十五里,旧为戍守处。”南宋末年,诸暨的何云父子在善坑岭抵御北兵(元兵)而殉难,后人建旌忠亭以示纪念。
元末朱元璋起兵,大将胡大海与张士诚曾在诸暨牌头、安华擂鼓鏖战。在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朱元璋属将朱文忠、胡大海攻克诸暨,张士诚为南下攻取浙中地盘,途经善坑岭。元代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张士诚部乘胜引兵自诸暨南攻东阳,依然途经善坑岭,最后为朱文忠所败。
在《崇祯义乌县志》之“形胜”中这样写道:“至策其要害,则尤有可言焉。邑据郡上流,扼东越之吭。元末张士诚自诸暨入寇,及我太祖下婺,先令胡大海攻取兰溪,西断喉咽已,乃亲提师旅,间从义乌躏入其深,而城遂附……愚观县治境界,独善坑一路接壤诸暨,行旅往来,开上江之门户,疆域巨防,无逾于此。然崇岗四塞,叠障周围,车不方轨,人鲜队侣,天下有事则据险拒敌,扼吭设奇,乌得百二焉。兵志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过’者,其在斯乎!”
善坑岭间龙祈驿
善坑岭是屏障,是关隘,军事力量在此据险而守,又是官方、民间交往的纽带与通途,南北使节、商旅与百姓在此交织,各种文化、货物与故事在此交融。如果说善坑岭是镇守千年的雄关要塞,那处于岭下的龙祈驿,则是消融霜雪的温情港湾。
从杭州至南昌古驿道历史悠久。据清乾隆版《浙江省郡县道里图》记载,义乌境内古驿道有:东南30里至东阳,南150里至永康,西南110里至金华府,北110里出境至诸暨。其中,南北两条驿道,穿越善坑岭向北出境可至诸暨、杭州,向西南越过航慈溪可至金华府,将两条古驿道连在一起,就是由杭州通往南昌的杭金古道。
元代的江浙行省驿道密集,从杭州至南昌古驿道在义乌地段属交通要道,元代在此驿道上置有龙祈驿。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龙祈驿,去县北五十五里。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佥龙祈站创置。今废。”另据清沈翼机等修《浙江通志》(卷八十九)之“驿传”记载:“龙祈驿,义乌县志:县北五十五里。元至元二十五年,佥龙祈站创置。今废。”
“佥”,是元代“佥事”或“佥院”的简称;“站”,即站赤,元代称驿站为“站赤”;“创置”,指始设该驿站。“佥龙祈站创置”的意思是:由佥事(负责)创建设置了龙祈站赤。
又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待贤驿,在县北三十里,唐置,宋废。又北二十五里(指在待贤驿北二十五里,即距县北五十五里)有龙祈驿,元置,并置龙祈站,明初废。”由此记载可知:一是在元代,设有龙祈驿,还有龙祈站,元代“驿”与“站”的并存,反映了其多元治理模式;二是龙祈驿在明初就废除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大刀阔斧下令整顿驿站,把一些“不雅驿名”改为汉名,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驿”,树立了明代邮驿的新形象。龙祈驿在明初就被列入了整顿之列。
古时的龙祈驿设在哪里?“去县北五十五里”是一个大致的位置,但不可能设于龙祈山附近。由《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分析:龙祈巡检司在“县北三十里”,而“龙祈驿”则在“县北五十五里”,两者相距了二十五里。如果龙祈巡检司设在龙祈山脚下的附近区域,那龙祈驿要比龙祈巡检司距县城约远一倍。
“去县北五十五里”之地又在哪里?古时驿站沿驿道设置,从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在义乌境内纵贯南北。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善坑(楼),县北五十五里。”另据熊人霖对《善关》一诗的注释:“善关,义乌北六十里。”
可见,“龙祈驿”应设在善坑村,紧依着善坑岭设置。此外,古代对驿站的命名也并非完全依赖于当地地名,还基于对当地的地理位置、历史传说、行政调整等多重因素考虑,善坑古时属龙祈乡十都,所以将设在善坑岭附近的取名为“龙祈驿”也不会有歧义。在今善坑村楼氏宗祠内就陈列有这方面的资料。
善坑村在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前后,由楼姓先祖为守父墓结庐于善溪演变而来。村旁除了这条经善坑岭通往诸暨、杭州的古驿道外,还有一条经白峰岭通往诸暨璜山的大道。因地处浙中通衢之地,村旁又设有驿站,故善坑在古时可谓鼎盛一时。当年驿站旁,设有饮马池,并林立着染坊、金店、酒肆与茶棚等诸多铺户,市井繁华,车马络绎。贩夫走卒穿梭往来,一派熙攘景象。
驿路繁华,倏忽映入眼帘:青石院落中,南腔北调与氤氲茶香融作一壶酽酽的暖意;槐柳荫下,马铃声与说书声交织成一路欢歌。忽闻关隘一声吆喝,惊起栖枝倦鸟,而驿站的树影炊烟,仍温柔环抱着天南地北的匆匆过客。
古岭今道车如流
滚滚车轮,驿路不再蜿蜒;青石板上,已不见马蹄轻叩的星火。龙祈驿的被废,比急递铺的消逝要早上数百年,因急递铺在《嘉庆义乌县志》中仍有记载。
明代的急递铺不只传递信息,也为往来官员和一般士商行旅提供食宿。因在善坑同设了龙祈驿、善坑铺,两者相处很近,故龙祈驿的废除或与急递铺的一些功能重叠有关。特别是随着使节往来的减少,为节省财政开支,龙祈驿在明初即被朱元璋列入了整顿范畴。
《万历义乌县志》在介绍“善坑铺”时附有这样一段文字:“按:乌旧有驿,以邑非冲道,使节罕临,革(指撤除)之便矣。但上司时取便道,横江乱流(指横渡江河),由诸暨入境,仅去一舍(古代三十里为一舍)。牌到候迎,辄逾旬日……宜于酥溪置一公馆,或仓厅(仓储的办公场所)亦可,岁佥夫役二名,带管扫闭,量给工食,委令中途传递驰报,庶候人夙戒(指提前准备),宾至如归,夫马免久候之劳,廪粮省虚糜之费,此亦公私两便之计也。”
上述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是:古时(在善坑铺附近)设有龙祈驿,只因使节罕临,就被废除了。鉴于依然有“上司”从诸暨入境,建议在交通节点苏溪设立接待点(嘉靖年间,位于苏溪附近的岗头铺、蒲塘铺已废除),既可让宾客到来时能得到妥善安置,人马不必长时间等候,又能避免粮饷的浪费,这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两全其美的好做法。
穿越千年的从容,昔年商队踏磨的青石板,今已被现代公路的沥青所覆盖,善坑岭早换了新颜。改革开放后,沿着善坑岭劈山造路,从诸暨安华到义乌楂林修通了公路,善坑岭也完成了历史使命,其中大段被削去建造了公路。处于善坑岭脚下的善溪水库于2011年3月开始修建,在2012年竣工,坝高达8.4米,处于山脚段的古岭由此也被淹没于水库中。在水库库尾虽还剩有一小段古岭,但已面目全非,几乎荒废殆尽了。
在善坑岭的岭顶及岭脚原各建有凉亭,单檐歇山顶,形象显露,具婉约秀丽风格。犹如江南地区的其它早期凉亭一样,这里的凉亭因建于驿道旁,既承担在官员文书传递途中的歇脚功能,为商队提供中途休整及安全保障,也可供行人作短暂歇脚、为田间劳作者提供遮风避雨的休憩场所。
其中,处于善坑岭脚的“善溪亭”至今仍存。在该亭的南北两面同设有拱门,门洞正对主路,形成穿堂之势,墙顶则采用反抛物线设计,如弓蓄势,却在刚硬的墙面中融入了一丝柔美。在东面墙体的左右各辟有一个圆窗,中空若镜。行人穿亭而过,山风贯堂,似能洞穿肺腑。穿过善溪亭,不远处即是诸暨的宣何街。在经年累月的风霜侵蚀下,如今的善溪亭亭顶早已坍塌,独余四壁仍倔强地刺向苍穹,让原本的“穿心亭”反成了“穿天”之势。周围丛生的杂草足有一人多高,唯有门楣上的“善溪亭”等字迹依旧清晰可见,似乎还在诉说着往昔的荣光。
据燕窝村村民介绍,沿善坑岭而建的这条公路,在近数十年间重修了多次。先是沿着善溪水库边缘修建了一条简易的乡村道路,能开拖拉机;后又沿着另一侧的山体修成了县道;在前些年,穿越善坑岭的S217省道开通,不但把道路拉直了,还将道路拓宽至双向四车道。昔时的崇山峻岭终成坦途,使善坑岭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时云外路,今已成坦途。那曾回荡于空谷的木屐声,渐被悠长的鸣笛取代;过去需耗时费力攀越的峻岭,如今只在呼啸声中一掠而过,化作车窗边飞速流逝的风景。若说古驿道犹如当时的“国道”,保障了政令军情的迅速传递,亦促成了民间信息的往来交汇;那么今日,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省道与国道的纵横贯通,曾在古代肩负交通枢纽之责的善坑岭,在现代路网中依然占据咽喉地位,必将为沿途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注入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动力。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摄
责任编辑:吴 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