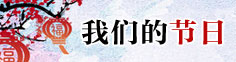文明播报
一曲溪流彻底清 廊桥飞架云溪南北

廊桥飞架云溪南北

义门街老街店铺 古驿道旁“众安亭”

今日云溪岸绿水碧
从诸暨宣何街入境,沿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一路南行,有一条溪涧与之形影相随,此溪即为善溪。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在诗句“丹梯傍涧弯”中提到的“涧”,指的便是善溪。善关地处善坑岭最高处,善溪一路向北流向诸暨宣何街,一路向南流向义乌的芦柴、义门街、楂林一带。
善溪由善坑岭附近的各山涧汇聚而成。待善溪流至芦柴附近时,与源于仰天岗、宦塘村域的十都溪(今朝塘溪)汇合;十都溪向南流至朝塘村附近的太平桥处,再与源于猪头山、从大畈流出的九都溪汇合,汇合后的溪流被称为云溪(今鸽溪)。
溪流是孕育生命的血脉,清澈的水流蜿蜒于山野之间,滋养着两岸的草木与生灵。在云溪沿岸,先民们伴溪而居,取水而饮,浣衣濯足。因此,溪流不仅带来生机,也承载着村落的故事,孩童在云溪的浅滩处嬉戏,青年人在溪水中抓鱼,老者则在岸边闲话,水光潋滟处,总有一幅水美人欢的鲜活长卷在悄然铺展。明朝中叶,邑人骆满(授四川布政司嘉定州州判)写有《活水潺湲》一诗,写出了云溪之水的清澈、灵动与生命力:“一曲溪流彻底清,鱼肥堪钓亦堪烹。沧浪歌罢多佳趣,濯足终须让濯缨。”
云溪流至楂林段,呈典型的“S”形流向。自义门街向西流经伏龙山(楂林村村民称之为后山)的山脚,再折向南侧的象鼻山北缘,然后向西流经村前,又向北转南,至钱宅有八都溪汇入后,继续往西南流至施宅处,与深溪合流后流入龙溪(今大陈江),构成了天然的太极地貌。而被群山环抱着的楂林村落则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盆地,正处于“阳极”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云溪改道,加上近年来伏龙山和象鼻山被挖,此地貌才被改变。
驿路溪声共悠扬,鱼跃清波草木香。汩汩云溪水,就像一位老者低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据说,此地在历史上常遭洪水肆虐,古人认为有蛟龙作祟,由此将上游称为云溪,取云上之溪的意思,而将下游称作龙溪,溪上现有“龙潭”。
云溪之源从善坑岭而来,从会稽山余脉而来,犹如在大地中奔涌的血脉,滋润着沿途村民们的心田,见证着沿途市镇村落的久远历史和沧桑巨变。由善溪、九都溪、十都溪汇合而来的这一脉清泉,直至流经楂林段,始终与古驿道相伴相随,水声潺潺,马蹄悠悠,水陆携手,共赴远方。
驿路通达万商集
明代的驿站不只为传递朝廷公文和信息而存在,还兼有商品贸易的功能。“驰驿之人,非尊官大人,则奉上命强有力者。”一些手中握有特权者,会利用驿递系统进行贸易,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在从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一侧的芦柴村,古时曾是一个较为繁忙的“集市”。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芦砦市,去县四十五里,在九都。”在古汉语中,“柴”与“寨”“砦”存在通假关系,“芦砦”“芦寨”即今“芦柴”。芦柴村距善坑不远,现属同一个行政村,地处旧驿路的斜对面。“芦砦市”在《康熙义乌县志》中还有记载,但在《嘉庆义乌县志》的记载中已“废”,说明此地的集市后因人气消退而没落了。
古时在芦柴桥头生长着一排参天大树,为往来的行人撑起了一片苍翠华盖。另在树干上还挂有草鞋、蜡烛等,可供在此歇脚的行人自取济急。村旁沿驿道开着一排整齐的门店,在善溪边置有凉亭、排凳等。每逢农历三、六、九楂林集市,前往赶集的和要过善坑岭的人们在芦柴桥头交汇休憩,他们三五成群,落座于凉亭、排凳处,饮茶听雨,高谈嬉笑。如果遇上农历五月十三楂林举办庙会,过往的商旅更是摩肩接踵。倦客如需住宿,人数不多可就地安排,需求量大时就得再走五六里路,赶往开有较多旅店的义门街。
义门街现为朝塘村的一个自然村,古时因有驿道穿街而过,可谓赚足了人气。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义门街,县北四十五里。”
义门街以骆姓为主。但因义门街地处古驿道边,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客商,故向来杂姓繁多。在这些行商坐贾中,有些待生意做得顺手了,积攒了钱财,便在此地置了田产,盖起了瓦房,定居下来。先是租赁铺面,继而买地造屋,渐渐与本地人通婚结亲,生儿育女,这些生意人也就成了本村人。日子久了,又不断有客商聚居下来,如此这般,村中的姓氏便愈发杂了。
在如今的义门街沿街店面,还留有一座立于清咸丰甲寅(1854年)冬月的门楼,青石垒成的基座,虽不似那些雕梁画栋的气派,倒也有几分威势。门楣上写有“吕成公祠”的匾额,只是受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这座公祠只剩下沿街而立的门楼了。
义门街自古繁华,沿街店铺鳞次栉比,各色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酒旗茶幌在风中猎猎作响,街市上行人川流不息。因在义门街不远的楂林有个“牛市”,多时有数百头牛上市交易,由此也带动了义门街的客流。一些至楂林赶集的商贩,头一天晚上便落脚于义门街,故每晚在义门街也有上百头牛寄住。
牛市的兴旺带动了义门街茶店生意的红火,一些茶馆、茶棚和茶摊等处总是门庭若市。每日清晨,茶桌旁挤满了人,有穿长衫的掮客,也有短褂打扮的庄稼汉。他们围坐在茶店内,高谈阔论,时而拍案叫价,时而低声私语。待买卖双方敲定了价格,一桩桩交易便在这茶香与唾沫星子中成交了。
据义门街的村民介绍,古驿道后来改造成了一条中间为青石板、两侧用鹅卵石铺就的黄包车路,街道内的这种青石板路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也就在十多年前,村里埋设自来水管网时,原来的青石板、鹅卵石路面才被彻底挖掉。
旧驿路沿着云溪再向南行走近二里,便来到了楂林。楂林是龙祈乡八都、九都、十都的交汇点,是金、衢、丽、温等地区居民通往杭州的必经之路,过往的商旅常在此歇息,装载着货物的宁波“盐担”也经常路过此地,周边的善坑岭、朱岭、后西岭、白峰岭则是通往诸暨的四条便捷通道。
据楂林的老人介绍,古时有“驿站”设在楂林附近,驿站备有马匹和“过山笼”(一种适合狭窄山路行进的简易轿子)等。显然,此“驿站”肯定不是“龙祈驿”,从至县城的距离分析,楂林距“县北四十里”,显然与距“县北五十五里”的龙祈驿不符。
楂林是义北、诸南的山货集散地。楂林的集市不但设立时间早,已有500多年历史,而且相当兴旺。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楂林市,县四十里,九都。”遥望当年,漫步楂林街头,商市繁华,大小商铺店号林立,行人熙熙攘攘;火腿坊、酒坊、南北杂货、客栈、中药房、染坊、马行等一应俱全;茶馆、饭馆、糕饼店、小吃店等遍布街面,楂林的民俗风物从当年繁荣的老街可窥见一斑。
楂林逢农历三、六、九为集市贸易日。每逢墟期,八都、九都、十都及诸暨南部的山民们,在天未亮时就拉来了杉木毛竹或竹木制品,有的则挑着竹笋茶叶、谷米豆麦、豆腐皮、山珍野味等,还有的赶着牛、羊,拉个独轮车运上猪崽。四面八方的客流汇聚于此,市声如潮。集市上卖什么的都有,现场交易活跃,其中行销较广的当数茶叶与竹制品等。
奉行忠孝继世长
云溪流经楂林,因受南岸小山所阻在原地踌躇了片刻,由此形成了一汪浅浅的洄水湾,然后折向西行,成就了楂林的这片小盆地。作为义北的重镇,楂林商贸繁荣、经济发达,是旧驿路上一处重要的墟市,与善坑岭附近龙祈驿的繁华遥相呼应。
楂林骆氏是骆宾王梅林派后裔。据明代谱牒记载,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讨武失败后,遭杀身之祸,株连家族。骆宾王第二子骆锡逃至龙祈乡九都泗洲桥隐居。古时,在龙祈乡九都建有“唐杰流风坊”。据《康熙义乌县志》记载:“唐杰流风坊,建九都。表初唐文杰骆武功宾王也。五都、六都、九都皆有裔。熊人霖诗:武功高去天三百,骆子才登第一峰。草檄能扶唐社稷,祠君可但作诗宗。”
至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骆宾王长子骆铨的后裔、骆宾王第十五世孙骆文起择云溪之滨、伏龙山之脚,依山傍水建宅,并引用了南朝宋文帝时期大臣张敷尽孝成疾而卒的忠孝故事,取张敷小名“楂”和骆氏原籍梅林之“林”,将居住地取名为“楂林”。
百善孝为先。骆文起将居住地取名为“楂林”,一是传达了张敷的“孝”,意在教育子孙如南史所记载的孝子张敷那样恪守孝道;二是以“林”为源,不忘梅林祖先,故亦为“孝”也。
“楂林”之孝义、孝德深植于后裔子孙中。楂林村内有一座昌忠祠,早期建于明万历丁丑年(1577年),后毁于兵燹,又几经改拆建,现祠为近年重修。在昌忠祠大厅内悬有历经400多年的“昌忠词”旧匾,匾之眉款写有“赐进士第义乌邑侯(对知县的尊称)李初荣书”,落款为“楂林骆氏宗祠,万历甲寅(1614年)”。“昌忠”,即“彰忠”,“昌”取彰明、光大之义。知县李初荣在题写此匾时,将宗祠的“祠”写作“词”。“词”为颂扬之语,强调的是对文辞的颂扬,突出文学贡献而非实体建筑。“昌忠词”,即通过文辞公开颂扬其忠义。
据村民介绍,昌忠祠是一座纪念骆宾王的宗祠,且不以姓氏命名。由此,此祠也成为骆宾王正气凛然、忠肝义胆精神的传承地。
楂林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要举办关帝庙庙会,此乃源自对关公的崇敬。关公忠义千秋,威震华夏,被后世尊为“武圣”。楂林在清朝中叶建有关帝庙,如今的关帝庙为上世纪末重建。而在民间信仰中,农历五月十三被视为关公的诞辰,故楂林在每年的这一天组织庙会。
关帝庙庙会是集祭祀、文娱、商贸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活动。在庙会举办期间,各路商贾云集,红男绿女汇聚,香客也蜂拥而来。十里八乡百姓成群结队来赴庙会,最大的愿望是能看上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据称,最多时庙会上有9个戏班同期搭台演出,还有多个罗汉班各献技艺,堪称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人文景观。
但随着时间推移,庙会逐渐演变成了物资交流会,商品交易更为活跃。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陆路交通和繁华的集市贸易,楂林一度成为商贾辐辏、百业兴旺的商业重镇。
在云溪东岸的古驿道边坐落着一座由清光绪皇帝下旨建造的“钦褒节孝”碑亭。此碑亭建于清光绪丙申年(1896年),高4米有余,三段式金刚座台基,单檐歇山顶,亭子四面均设月梁,梁上雕饰仰莲瓣纹,亭之所有构件均为红砂岩石打制而成。亭内原立有一通两米多高的石碑,碑上刻有圣旨“钦褒节孝”四个大字,并详细记述有“建亭以志节”的缘由及朱氏的事迹,现碑已毁。
“钦褒节孝”碑亭为旌表浦江朱氏而建。该碑亭现为市级文保单位,周身环绕于一片茂密的篁竹中,风过疏竹簌簌作响,似在絮絮低语着过往的故事。
古驿新街绕清渠
一条古驿道,就像一条黄金线,串起了善坑、芦柴、义门街、楂林等沿途市镇村落的繁华。这云溪,又如一条绵延的脉络,沿着古驿道奔流不息,形影相随。已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金普森对儿时所走过的这段旧驿路刻骨铭心,在生前曾专门著文回忆了这段经历。
金普森的老家在外西坞村,出村走上200米的乡间小道,即步入经千年风雨洗礼的古驿道。途经芦柴、西岸凉亭、义门街,走过又高又长的木桥,就到了楂林。他在文中这样写道:“芦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设的廊道,廊道西边是善溪,廊道东边开有几家商店,印象最深的一家是怡升堂中药铺。在芦柴到义门街的古道间,有一个‘众安亭’(俗称西岸凉亭)可供路人歇脚。‘众安亭’三字是我爷爷写的。从凉亭开始,走上不到千米就到了义门街。义门街长200米,南北走向。街道东边是九都溪与十都溪,两溪溪水会合后称云溪,西边是农户、商家,睦邻而居。沿古驿道开了几十家商店,印象特深的是一家打铁铺,每次路过义门街时,就能听到打铁声和云溪的水流声。”
虽历经千年,从众安亭到太平桥路段,如今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驿道路基,但原先用来铺设路面的青石板与鹅卵石已消失殆尽。加上长期少有人走,古驿道已变成了黄泥路,淹没于半米多高的荒草中,唯有伴其左右的溪流依旧。正如孟子所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众安亭,如今依然盘踞在古驿道上,部分墙体出现了裂痕,已让人体会不到“众安”了,而藤蔓却死皮赖脸地攀附于它生长着。亭内挤满了各种农具和杂物,似乎变成了时光的“仓库”。田野的风吹拂着悬在凉亭横梁上的薄膜碎片,猎猎作响,仿佛在重复着“商旅曾在此歇脚”的老故事。时光不语,却把答案刻写在了凉亭灰白的老墙上,那涂满字迹的墙体,仿佛让记忆有了容身之处。
云溪之水潺湲,却也未曾停歇。在溪流西岸的义门街,依然保留着部分清末民初的砖木结构商铺。从那斑驳的木排门,以及狭窄的街巷格局中,依稀能感受到旧时市井的气息。几幢体量庞大的徽派建筑沿街而立,错落层叠的马头墙在夕阳中勾勒出锯齿般的剪影,更有那精美的梁枋斗拱,似正俯瞰着一辆辆共享单车沿街掠过。
这临溪延伸的古驿道,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过往繁华的记忆。当行人走至楂林村边,就可以看见有座古廊桥横跨在云溪之上,桥匾上写着“云溪廊桥”四字。该廊桥长达44米、宽3米,青石板桥面,樟木栏杆,青灰琉璃瓦屋面。走上廊桥扶栏相望,但见水清岸绿,天光云影,偶有鱼影掠过。如今,这里成了村民们最喜欢的休闲场所。从写在廊桥柱子上的联句中,人们可以读到往昔旧商号的市声与年轮,以及那些被溪水反复淘洗却愈见精神的忠孝与节烈。
对于当年的盛景,明朝中叶邑人骆满曾在《楂林纪胜》一诗中留下这样的印记:“我家楂林中,一览景无穷。灵秀本天巧,开鉴自鸿濛。奇峰峙南北,活水流西东。乔木接阴霭,修竹招清风。看花乘逸兴,采药寻仙踪。樵唱依深谷,渔歌卧短篷。黄鹂啼翠柳,白鹭巢苍松。比景将谁拟,钟山胜颇同。”
虽然,昔日的胜景已经远去,但那沉淀于古驿道上的一道道车辙中,仿佛还回荡着往昔哒哒的马蹄声;倾听沿古驿道日夜奔流的云溪流水声,仿佛有诉说不完的商旅往来故事。褪色的路碑不再是匆匆的行程,而是放慢的脚步,为的是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安宁与诗意。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